教与学的好传统
回忆上世纪60年代在戏文系学艺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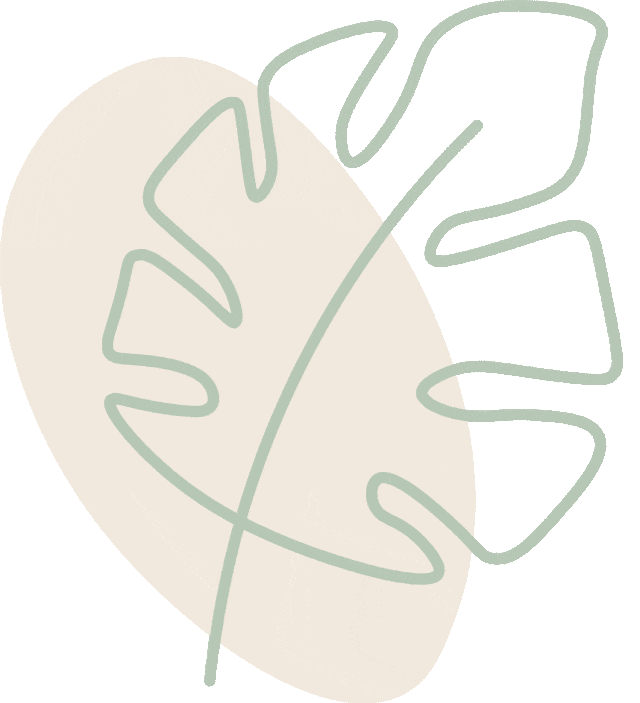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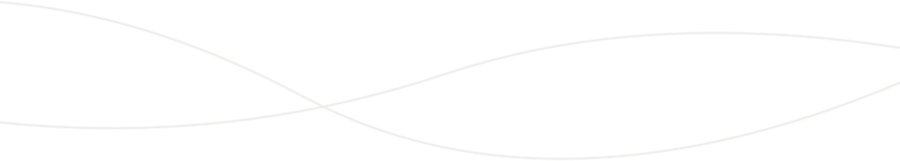
我学的是“戏曲创作”,1963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毕业,分配到一个区剧团担任编剧。回顾我在戏剧学院学习时,老师们的传艺,让我终身受用,他们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,对我终生难忘。
学校老师是个群体,从现在回顾“当时的”气候——上世纪60年代初,知识分子(特别是“大知识分子”)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、“改造”。 “戏文系”刚新建,围绕建立“戏剧创作”的理论,教师们可能也是一个“新”的组合和筹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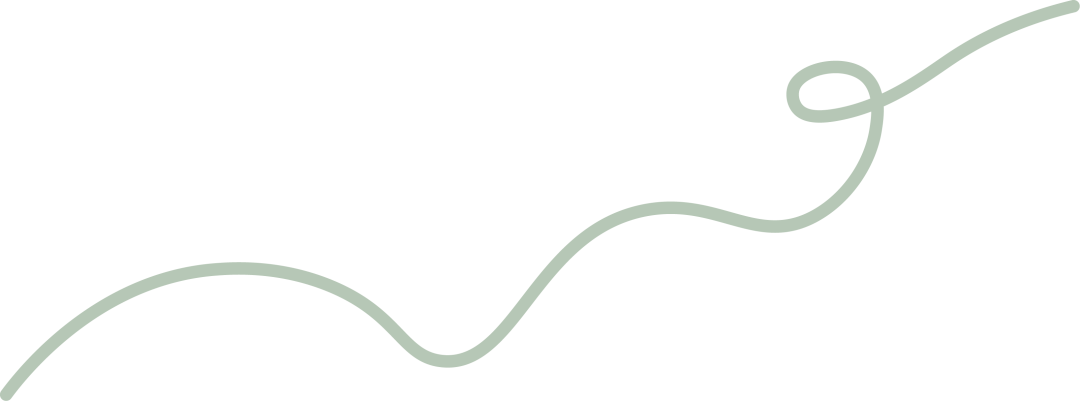
他们的教学实践和给我们的印象——个个“兢兢业业”,对学员“谆谆善诱”。魏照风老师开设的“中国话剧史”,顾仲彝教授创编的《编剧概论》,陈汝衡老师的《写作实践(戏曲唱词写作)》等等,我理解都是“新建的”学科,他们有一整套学术的理念和积累,教学时——口传心授,耐心、恳切地教诲、诱导。例如,魏照风老师的《话剧史》,当时以回忆“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周年”的史料为教材。顾仲彝老师的《编剧概论》,更是观点鲜明,条分缕析;他开宗明义就对编剧提出了思想(要有正确的世界观)、生活(丰富的社会实践)、技巧(掌握编剧基本艺术技巧)“三必备”(但是都是以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为准绳)。在讲解“没有冲突就没有戏”时,不仅列举了古今中外大量的实例;并且结合当时《文汇报》等发起的“社会主义新喜剧”大讨论,提到“歌颂性喜剧”有没有、要不要设置“戏剧冲突”时,他又从大量的喜剧实践中,从“差异就是矛盾的开始”的角度,来完善“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”的理论;并总结了“喜剧的情节,(人物的)喜剧性格,喜剧语言”的“喜剧创作”的“三要素”。这些创造性的理论,联系实际的独到的学术见解,对于当时我们这些热爱戏剧创作,却又“一知半解”的学生来讲,无疑是真正的“授业解惑”,对我们有着强大的吸引力。

中国曲艺理论家 陈汝衡
再如陈汝衡先生为我们教授的十分有特色的《写作实践》,实际上是教我们怎样写作戏曲唱词。我们都是高中毕业,那时提倡“厚今薄古”,我们的古文基础都比较差。
陈先生胖墩墩、福德德(沪语音译,意为有福相)的身躯,上课时脸上始终架着一副眼镜,只有在查看我们的作业时才取下眼镜。他对我们的作业,常常一边看一边用他那纯正的扬州话说着“不臭(错)!不臭(错)!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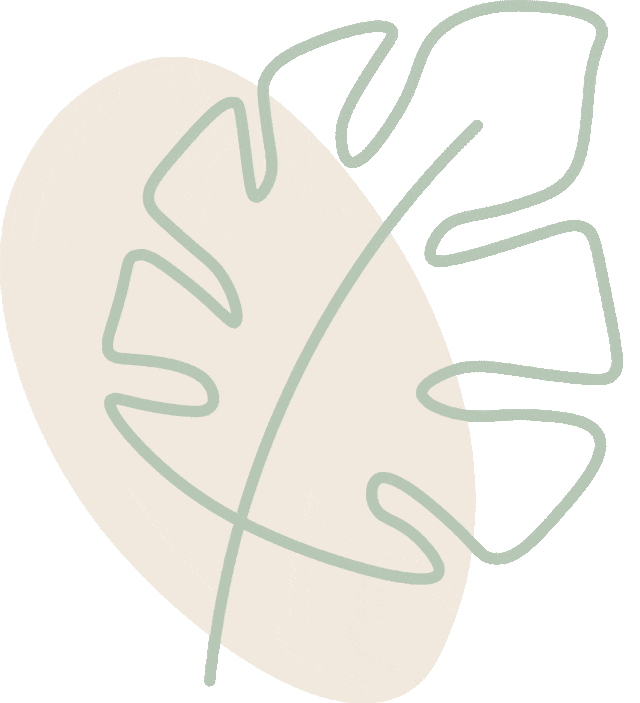
1955年推广普通话以后,取消了“入声声调”,这对于学习古诗韵律造成了困难(古诗、戏曲唱词都将入声字归入“仄声”,普通话取消了入声声调,把很多入声字归入平声声调了——造成混乱)上海方言原来“入声字”一讲一听就能分出,在普通话“推广后”,都乱了。班上还有一个山东籍的女同学,根本不会区分入声字。陈老师给大家“开小灶”,引用大量的古诗词诗句实例来讲解“入声字”的特点,又在我们学员练习写作唱词时,训练大家学会平仄押韵,他的“写作实践”课最大的特点是当堂布置题目当堂批改作业。一次,他要我们当堂练习写《牡丹亭》里杜丽娘的“上场诗”,我写了“蘭质无心理粉黛,春光有意织相思”的对句。他走到我桌边,取下眼镜看了我的草稿,很快地将“理”字改成“施”字,还对我轻轻地说了声“平厌”(提醒我学会用字锤炼平仄声),旋即戴好眼镜,去黑板上抄写了这个对句,还连声说:“不臭(错)!不臭(错)!我们班里有不少人是会写的!(他把“写”字讲成sie音)”一种赞不绝口的样子。我受宠若惊,这一来竟大大激发了自己学习的积极性,每次做学写古诗或上场诗的作业,都更加认真卖力。陈先生诲人不倦,批改作业十分认真,常常为我们逐字逐句修改,教我们斟酌推敲,有时甚至帮我“通首改韵”;还在我的作业本上留下“平仄稳当,可用”或者“颇佳”的批语。可以这么说,我们班不少同学都是在陈汝衡先生手把手下学会写作韵文唱词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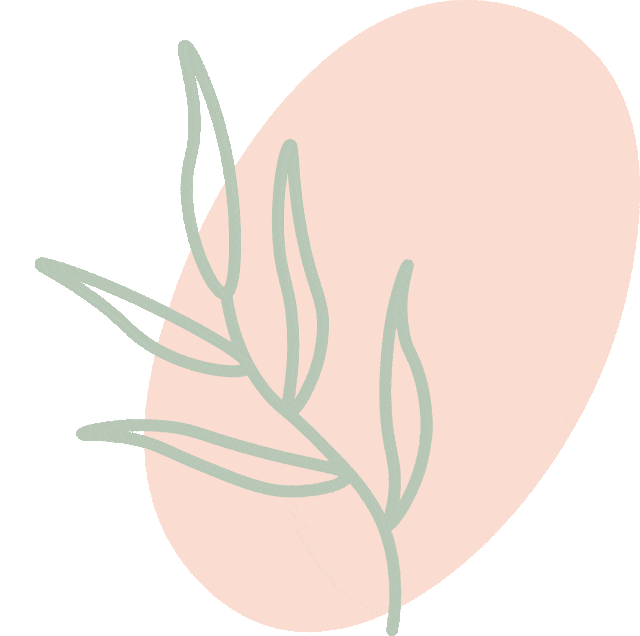
可能现在的学生跟我们有些不同,虽然大家都是热爱戏剧创作的,但我们当时大多是“白纸”,把老师给的都奉为“真谛”,对老师虔诚,崇拜,如饥似渴地学。但老师们经常教育我们独立思考,启发我们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实践和创造。现在的学生可能“看得多,见得多”了,也许认为老师“不这么样”;刚刚学,或者还没学,已经觉得要“创新”了。这是很不好的!应该对学生一开始就进行入学教育,在理念上、学习方法上,端正他们的认识。“学生以学为主”,也应包含学生主要任务是“学习、继承”的含义。老师的教学讲的是科学规律,“创新”必须遵循科学。创作不繁荣,与不下生活,违反创作规律,大有关系。

讲稿:徐维新

